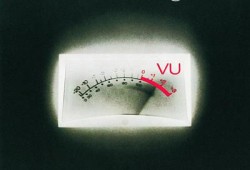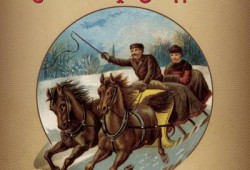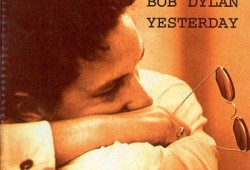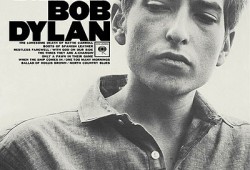哥斯拉对战摩斯拉 ──【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
- 专栏
- 2021-04-17
- 167

鲍勃·迪伦与安迪·沃霍在1966年1月初次见面之前对彼此一无所知。虽说沃霍是“地下丝绒”乐队的导师──那其实是他圈内成员硬加给他的──他喜好的流行音乐其实是那类做作讨喜的曲子,像《我的男友回来了》和《Da Doo Ron Ron》之类。当时安迪的朋友们告诉他,迪伦在《像一块滚石》中嘲笑了他(以及他与伊迪·赛奇维克〈Edie Sedgwick〉的关系),它像一部短小的新浪潮电影,大致讲的是一个愚蠢的交际女子和他无知却又装模作样的导师(也就是沃霍)。歌里那个外交家骑着铬黄色骏马,肩上站着只暹罗猫(安迪是个严重的猫迷),结果却发现那一切并不重要──我们可怜的女主人公直到自己被他窃取一切才发现这一点。
虽然在1965年12月之前,迪伦与伊迪还未被人引见相识,但是据后来所谓“沃霍电影”的导演保罗·莫里西(Paul Morrissey)指出,“迪伦可能碰巧在夜店遇到了安迪和伊迪,他迷上了她。马上决定要夺走她并且最终得手了,然后他又很快抛弃了她”。
迪伦,虽有一帮嬉皮朋友并且常去现代艺术博物馆,但他似乎对波普艺术(pop art)没什么了解。像那时的很多人一样,他大概还认为波普艺术是个新奇的小玩意儿,就像呼啦圈什么的。但沃霍这个人使他对此有了兴趣。沃霍不仅是一个画家,他像迪伦一样成了六十年代的标志。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就是六十年代。沃霍的图像是无法抹掉的,因为他的画、他的电影暧昧又难以理解。而他的“工场”内景又给他笼上了一层怪异和邪恶的阴影,他又把这种印象转入了“马克思堪萨斯城”(Max's Kansas City),他夜晚常在那的密室里笙歌艳舞。
鉴于迪伦天生的好奇心以及安迪对名望的追逐,他们的会面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迪伦马不停蹄的巡演和录音,他得有什么特殊的动机才会考虑造访沃霍──那便是伊迪·赛奇维克了。

(伊迪·赛奇维克,Edie Sedgwick)
迪伦与沃霍的会面正巧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伊迪,沃霍命定的超级明星,她正在忧虑被安排在他的电影里饰演越来越多的贬值角色──而且还得不到报酬。鲍比·纽沃斯出场了,这个富有魅力的纨绔子弟、艺术家与民谣歌手,他还是鲍勃·迪伦最密切的朋友以及混世合作者。伊迪两星期前正好在迪伦最喜欢的据点──“野炊”俱乐部──见到纽沃斯。她崇拜迪伦,但却与纽沃斯展开了一段情事。
“夜总会里很紧张,主顾们翘首等待。每个人都在说着,‘鲍比来了,鲍比来了。’”摄影师奈特·芬克尔斯坦(Nat Finkelstein)说。在1966年1月的那天,迪伦及其随众访问安迪·沃霍的工场。电梯门开了,迪伦、纽沃斯还有一个摄制人员走了出来。“迪伦举止很酷,”沃霍的一位助手杰拉德·莫兰格(Gerard Malanga)回忆道,“一直闭着嘴。不论对谁说的话,他都是这样回应,‘哦……?是吧……’”
“迪伦来的那天气氛是如此的冷,”工场里的常驻摄影师比利·内姆(Billy Name)说,“迪伦是那么冷傲,不搭理人。杰拉德把他带进来并向安迪介绍,而他们居然握了握手。我们已经做好了‘试镜’(screen test)(安迪·沃霍创造的一种实验电影类型,他拍摄的这一系列电影大都是几分钟的默片)的准备。所以很快进入了工作。”这次访问的表面说法,至少在安迪眼里,正是这试镜,为了用一个固定摄像机拍摄一个三分钟的默片。
试镜是沃霍之莫测天才的发明之一。很多名人都来过他的工场,他在第四十七大街的工作室──安迪怂恿人们顺便来玩──但是遇到腼腆、不善言辞,或者无礼无知、气场慑人的客人,他的对策就是请他们坐下然后拍摄他们。在这三分钟拍摄时间里(一卷博莱克斯胶片的长度),隐藏的情绪就会无意地流露出来──偏执,傲慢,变化不定,产生了一些二十世纪末最让人惊讶的人物特写。出现在沃霍的试镜中的人包括: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卡斯·埃利奥特(Cass Elliot)、艾伦·金斯伯格、妮可、娄·里德(Lou Reed),还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他们会被以十六帧每秒的方式拍摄,产生一种奇特的、凝滞的效果。

“通常我们完成一次试镜后就会听到人们说笑聊天,但是迪伦不会,”比利·内姆回忆说,“当时就只剩下不舒服、冷淡和无动于衷了。而安迪意识到他几乎无能为力,而不是像他以往的做法,让一切都顺畅起来。”但那样可不行,也不能行。据莫兰格说,自从走进工场,迪伦就对沃霍和他的氛围产生了一种厌恶。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正在一个同性恋、瘾君子的温室里而感到恐慌──他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沃霍是同性恋。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在绯闻专栏里他和伊迪被谈论着,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衣着风格──皮夹克、牛仔裤、靴子还有墨镜,几乎跟迪伦一样的行头。尽管在六十年代中期迪伦爱好雌雄同体的造型,但他和纽沃斯以及随行们是一帮异性恋的放浪者,他们以摩托车和枪支这些男子气的玩具来自娱自乐。
这两位六十年代巨人的见面是具备产生深远影响的可能性的,但是迪伦对工场的访问,按照莫兰格的说法,“不算什么事件”。就凭当事人都在努力耍酷,又怎么会是其他的情形呢?“那完全是两个难以沟通的人在相互无视,”保罗·莫里西说,“安迪印象深刻,因为迪伦是那么大名鼎鼎,可他又是如此吝啬,可恶,故意地一言不发。他那种药物上瘾的类型使他非常疏远和自我隔离。他属于瘾君子里面比较逃避的那种,但是内在的他一定是易怒的,仇恨的,就像常见的这类人一样。在他漫长的演艺生涯里,我可从没听说过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人。而当他跟鲍比·纽沃斯混在了一起,情况就更糟了。”
“马戏团正巡演到镇上,”芬克尔斯坦说,“安迪处在一种强烈的焦虑中。一个个性压过安迪的人造访,那可是件大事。不用说,安迪被吓到了。这两个牛掰的家伙算是撞在一起了。”谁都以为这个会面将成为一次经典的流行文化事件,甚至是一次历史机遇。但就像其他一些被强烈期许的名人聚首──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与查尔斯·狄更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与赛奇·爱森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萨尔瓦多·达利──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沃霍与迪伦都不是出色的交谈者,而当另一个名人在场时,安迪总是装腔作势,他完全不是个热情的人。沃霍的冷漠面,跟迪伦一样,是其形象和艺术的一部分。现场的温度几乎是骤降。
奈特·芬克尔斯坦拍了那些照片。即便在一个如此尴尬的会面中你仍然需要留影。“他们的会面是经过仔细谋划并且精心安排过的,”芬克尔斯坦说,“迪伦、纽沃斯和安迪坐在一起,不过那样的安排是基于录音的需要。我告诉安迪和鲍比戴上墨镜然后直视镜头。他们谁也没有彼此呼应。那个场景让我联想到某个弗兰德画家笔下的三位商业巨擘,而我就是那样拍他们的。”

那是巨人的交锋。谁是最“嬉皮”的?谁才是最酷的?由于迪伦对安迪毫无索求,而他来这儿的原因──伊迪──并不在场,所以那天他胜了,但也不是一个愚蠢的错误都没犯。
“‘试镜’一结束他们马上开始为拍照摆姿势,”沃霍的朋友罗伯特·海德(Robert Heide)回忆说,“迪伦起身径直走到一幅画前,画上的埃尔维斯一副牛仔打扮,举着枪(几幅双重埃尔维斯画像倚在工场的墙上)。他说,‘我想我得买一幅这个,老兄。’那是我仅有的第二次看见安迪害羞了,就是一种不安的样子。有人决定要买了!”
但是根据莫兰格的说法,这并不是事情发生的准确情形。“迪伦没有强买那幅埃尔维斯画像,是安迪主动拿给他的。安迪有意挑出了埃尔维斯。当时的情形并不是他把一堆画都摆出来的。他琢磨过,‘啊,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歌手;鲍勃·迪伦,也是歌手。’”
而且,如比利·内姆的解释,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那并不是为了‘试镜’,安迪希望有机会继续互动。说不定迪伦会请他为专辑创作封面。安迪拿出礼物希望彼此继续联系,而迪伦坦然接受,把那幅埃尔维斯当作那三分钟‘试镜’的报酬带走了。他关上门就那么走掉了。”
鲍比·纽沃斯帮迪伦把那幅画抬进电梯,下楼然后走上大街。他们把画捆在旅行车的顶部(“像是反季节捕猎的梅花鹿。”芬克尔斯坦说),把它带去了迪伦在伍德斯托克的家。他对它除了蔑视没有表现出别的。据可信的说法,他把它头朝下挂着,放进橱柜里,或者用它当飞镖靶,或者更糟糕。据莫里西说:“很多年以后,有人去拜访迪伦,在他的阁楼或者其他住处看到了安迪的埃尔维斯画像,一条紧身裤穿过了他的胯部。安迪真的非常恼火。在某次谈话里他说,‘天,那可值一大笔钱。他不该那么做。’不用说,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比当初安迪送出的时候要值钱得多了。”

不管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迪伦显然并不理解那幅画的价值或者并不在意它。“我不想要这个,”他告诉艾尔伯特·格罗斯曼,并补充道,“他干吗给我这个?”他拿它换了格罗斯曼的沙发,但是最终鲍勃成了笑话的对象。1988年,格罗斯曼的遗孀莎莉,以七十二万美金的价格卖掉了那幅画。现在它的价值更是远超当年。
安迪要见迪伦并且拍摄录像的目的并不难猜测。安迪是个疯狂崇尚名望的人,而且显然他对迪伦的大名和冷酷魅力感到敬畏不已。他大概以为他能让迪伦出现在自己的电影里,或许跟伊迪演对手戏,而她不会为他而成为叛徒。可是迪伦对电影有自己的想法,也许某些想法包括了伊迪──但绝不包括沃霍。
是迪伦在一段时间里促成了与伊迪合演一部电影的可能性。伊迪的魅力来源于其中性化气质产生的吸引力与拒斥感(这一点是伊迪与其父关系的映射),迪伦看出,伊迪做搭档会是自己理想的陪衬。但是迪伦在创作他的神秘主义电影故事时——比如《雷纳尔德与克拉拉》(Renaldo and Clara)──总是问题重重。电影,即使其最朦胧的表现,也远比歌词(特别是迪伦的歌词)具体,所以也就很难与他精心调制的神秘感相契合。
沃霍—伊迪—迪伦的三角游戏转折点在格林尼治村的某个下午来到了。当时安迪要去找皮匠选一些外套,并且打算到“野炊”俱乐部见罗伯特·海德。这时候伊迪已经以某种方式和迪伦产生了联系──那是艾尔伯特·格罗斯曼正在筹备的一部电影,而这已经引起伊迪与安迪之间的一些紧张。
“我到了那儿,”海德说,“却看到伊迪──安迪还没出现──她坐在那里喝着一杯白葡萄酒,脸上挂着泪。我说,‘发生什么事了?’而她就开始咕哝着,‘我没法接近他了。我努力亲近他却不理睬我了。我想一切都完了,结束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后来明白了她原来是因为安迪而忐忑不安。安迪会变得异常冷漠,特别是当他感觉别人要离开他时。这时安迪来了,带着一台电视机,穿着蓝色的山羊皮外套,用他耳语般的声音说,‘噢,嘿,噢,嘿!’他戴着墨镜,点了一杯啤酒,我也点了杯啤酒,我们就那么枯坐着。”
“没过几分钟,一辆豪华轿车停在外面,然后鲍勃·迪伦走了进来──这大概是《无数金发美女》时期──迪伦走过来坐在了伊迪身旁。没说什么话,但显然他们之间已经有难以置信的亲密。安迪向他们投来质询的目光──那目光几乎要杀人──然后他撇开了视线,而伊迪斜睨着,最后,在近十分钟几乎没人说过几个词的时间之后,迪伦说,‘我们走吧!’然后他们就出去上了轿车。安迪一言未发。他只是喝完了他的啤酒,然后我们离开了。你懂的,这种事情在永远酷极了的‘工场’,类似于安非他命还有莫谈感情之事。我是说,那天的伊迪不太寻常,因为就我所知,到那时候为止没有人真实地袒露自我。而那一刻是个转折点。就在伊迪跟迪伦走掉的时刻,他感到了怎样的背叛,安迪一定深深隐藏起来了。”
正如所有只在社交层面见过伊迪的人印象中的,她是个耀眼的女人──她有趣,很酷,美丽,而且有天赋。她设计自己的服饰,体现着六十年代中期的终极时尚形象,而且她似乎是那种具备无限变幻可能的人。迪伦,纽沃斯,还有格罗斯曼使她以为他们要为她打造一个演唱生涯。问题是,她毫无演唱的才能。所以在她跳槽去了迪伦一派之后,经历了一场残酷的醒悟,根本不会有什么演唱生涯。
“伊迪被鲍勃·迪伦可憎的经纪人艾尔伯特·格罗斯曼控制起来,”莫里西说,“他禁止她跟安迪见面,虽然安迪也永远不会再播放她的影片,因为他们将毁掉她的艺术生涯。”

“虽然前景是跟鲍勃·迪伦演出一部电影,”雷蒙斯乐队(Ramones)的前经纪人、迪伦的朋友丹尼·菲尔兹(Danny Fields)说,“但是格罗斯曼从来没有为她做任何事。他们有过一些谈话,大都是消极的,关于安迪。他们会对她说,‘你知道你真的可以自由行动,你会是个真正的女演员,你是那么漂亮,你正变得那么瘦,你为什么不去跟那些嗑药的同性恋随便转转?他们才不会为你做什么。’你瞧,她是他们的一个新玩具。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生气地要回到安迪那儿,我想他曾经向她靠近过。但是她越来越堕入毒品。而且她的这个耗尽一切的行为与鲍比·纽沃斯有关。”
纽沃斯曾说,他认为伊迪去拍那些“愚蠢的沃霍影片”是在浪费她的时间。那么你倒是要跟伊迪拍什么样的电影呢?纽沃斯制作了一部短小的“卓别林式”(他的描述)电影,片中伊迪在复活节的游行中,把一只穿着滑轮鞋的犀牛推上第五大街,警察们则假装给她开了非法停泊厚皮动物的罚单。几个月过去了,很明显根本没有什么鲍勃·迪伦电影要开拍。
“迪伦和格罗斯曼曾经对她感兴趣,是觉得她可能是鲍勃电影的一个合适搭配,”莫兰格说,“但是当他们发现她是个没什么天赋的花瓶时,就放弃了她。”
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同意,迪伦和伊迪的恋情只是个流行神话。“那是一个策划。”莫兰格说。充满幻想的伊迪与迪伦的恋情故事被人以言情小说的场景描绘出来(就像电影《工场女孩》里,当伊迪与“迪伦”在他伍德斯托克的隐蔽居所缠绵时,壁炉里的原木正噼啪作响)。“那只是个传说罢了,一个编造的故事。”比利·内姆说。不过,丹尼·菲尔兹说,他有二人私通的证物:那顶豹纹圆筒女帽。
“据说他写的那首《豹纹女帽》就是关于她的,”菲尔兹说,“你知道,她确实有一顶那样的帽子。她还有一件豹纹外套,我估计那是她从谁那里偷来的。她把那顶帽子落在我的公寓里了。人们说,迪伦为伊迪写了各种各样的歌曲。是《眼神哀伤的低地女子》还是《就像一个女人》(Just Like a Woman)?我觉得如果你问迪伦他的这首或那首歌写的是谁,他自己都不清楚。我认为现在这些全都是假的。我认为全不是那么回事……没什么真相,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记忆。特别是当你谈起四十年前的那些事。”
迪伦自己,这位声名狼藉的、喜欢闪烁其词的被访者以及历史的改写者──他的和别人的历史──在1985年对一位采访者说:“我与伊迪·赛奇维克从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我曾经……读到过说我有,但其实我对伊迪没有太多印象了。我记得她确实出现我的圈子里过,但我知道其他人,至少据我所知,可能和伊迪有较深的关系。呃,她是个很好的女孩,一个令人激动的、非常热情的女孩。她曾在安迪·沃霍的圈子里待过,而我无意中进入又离开了那个圈子。”
在某种意义上,迪伦确实与伊迪制作了几部影片。他那张“黑色电影”般的专辑,《无数金发美女》,里面尽是暗夜里的怪人,迷失者,嬉皮士,骗子,它们似乎正是从伊迪所生活的泛着磷光的夜晚世界里走出来的:你发现自己身处所有这些怪异之所的夜晚,在那里陌生的人们做着奇怪的事情,你却难破重围无法脱身。由于迪伦对神秘形象的热衷,对他来说,伊迪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人物类型,透过他的夜视镜看穿的,是一个倒霉的、难懂的落难女子。作为难以俘获的、颓废的女性,一个失魂落魄的情人,一个“像小女孩一样崩溃”的女人,一个魅惑的毒瘾歌妓,她的感染力能够让他体悟底层世界,伊迪作为欲望的多变的载体,就生活在《无数金发美女》专辑里面。
听迪伦,一个总是非常受欢迎的游戏就是猜测这首歌或那首歌里说的人到底是谁。在《又和孟菲斯布鲁斯一起困在汽车里了》(Stuck Inside of Mobile with the Memphis Blues Again)这首歌中,你听到露西(Ruthie)在老酒吧里告诉他,他那位幼稚的名媛(伊迪)只知道他需要什么,“可是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就有了那个范本式的伊迪,《像一个女人》里的孩子般的女人。关于伊迪,你不会得到比那首歌里的雾霭、安非他命与珠宝更生动的写照,或说比它更精彩的诗句了,关于一个人格分裂的情人,刚刚还是完全性感自若的美人,却顷刻间成了破碎分崩的玩偶。
从1965年到1966年迪伦的一系列歌曲,不管它们是或不是同一张专辑,歌词里面都藏着伊迪的影子。他最令人难忘的一句是《乔安娜的影子》里那句:“炽烈情感的幽灵在她面孔下哀号”(The ghost of’ lectricity howls in the bones of her face),就像是对伊迪的痛苦焦虑进行了 X 光透视。在伊万·卡普(Ivan Karp)关于伊迪的令人不安的回忆中,“她心里乱得一塌糊涂”。
沃霍后来对迪伦的态度是轻视的(就像对大多数人的态度)。“迪伦,”沃霍说,“从来都不真实──他只是在效仿真实的人,而安非他命则用幻术塑造了它。安非他命让他能够抄来一些合适的词并且听起来还不错。不过那个男孩从来没有真情实感(笑起来)。我从不买他的账。”
迪伦后来对那次会面至少做了某个方面的道歉:“我曾用一幅安迪·沃霍的‘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做交易换了一个沙发,那可是个愚蠢的做法。我一直想告诉安迪我做了多么蠢的事情,如果他能再给我一幅画,我绝不会再那样做了。”

考虑到迪伦—沃霍之晤匪夷所思的结果,它所浪费掉的机遇却有一个长时间的续写,以臆测和调侃的方式,最近的例子是《鲍勃讨厌安迪》(Bob Hates Andy)卡通系列。在片子里面,鲍勃对美国发出深刻而刻薄的评论;而沃霍,至少在剧集开始的部分,被表现为一个白痴购物狂,并且他总在嘲笑迪伦高尚的社会热忱。尽管在剧集里,迪伦比安迪外形更酷,更招人喜爱,但他在1966年时显然已经跟当时的前卫艺术不同步了──比如,他没有“抓住”波普艺术,从气质上来说,他更接近抽象印象主义艺术家。
迪伦的天才在于把现代主义的创造物融入了流行音乐,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现代主义已经被中产阶级文化吸收了──卡夫卡与乔伊斯已经在高中课本上,绘画初学者们已经被鼓励像毕加索和米罗那样涂抹。“前卫派”也继续前行了,他们嘲弄着老派现代主义者的价值观,那些由原创性、激情以及孤独所激发的天才(就像我们看待迪伦的方式,以及他看待自己的方式)所构成的价值观。安迪是一个化身,他代表着新的美学:后现代主义。除了拒绝所有这些虔信之外,后现代主义还解决掉了老波西米亚们对金钱的轻蔑。他们是艺术家,而他们的工作是──刺激那些虚伪的自由主义者:“冲击中产阶级!”(Epater la bourgeoisie,在任何时候拆穿中产阶级愚人的伪装。)法国十九世纪末在艺术家中流行的一句口号。
那部系列动画,“似乎”表现了迪伦与沃霍之间可以想象的种种交谈。它们其实是创作者约书亚·西塞罗尼(Joshua Cicerone)的道具罢了,作者借由它们演绎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模型。在一次凯文·约翰斯(Kevin Johns)的采访中,西塞罗尼承认,“某种意义上,它们其实是我自己心灵交战的双方”。
《鲍勃讨厌安迪》实质上是一个分裂的文化在自我辩论,借用迪伦和沃霍作为符号的形象而已。“我没法不把这些人看作文化意义的高塔,”他说,“我热爱音乐家迪伦。我依循沃霍的观念启示而生活。而两位艺术家都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技巧。他们是天才的现代原型。我视他们为现代的、自由主义的、多变的、城市知识分子视角的绝对典范。我明确地把他们看作文化的对话。”
迪伦和沃霍已经成了漫画般的、文化的、神圣的怪物,而1966年1月那次简短的会面则产生了一个不断演化、变幻装扮的文化冲突──一个从不太谨守事实的冲突。安迪从不自称天才──那会违背后现代主义者的剧本。而西塞罗尼,比如说,尽管《荒芜的街》是在迪伦访问工场前的六个月录制的,他似乎还是相信《荒》写的就是安迪的工场(真的?那怎么解释得通?)。好吧,迪伦从后现代主义里带走了一个方面。如果你需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后现代主义,它便是“挪用”,这是迪伦在新世纪里变得非常擅长的一种手法。
(本文选自 《他是谁?探究真实的鲍勃·迪伦》 ,点击书封可直接购买此书)
《他是谁?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
作者:[美]戴维·道尔顿
译者:郝巍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小阅读Random)

这是首部关于那位最伟大的嬉皮士的真正的“嬉皮式”的剖析力作。──蓝尼·凯耶(Lenny Kaye)
鲍勃·迪伦。我们所听说过的流行文化人物中,他是受到最多检视的一位。在图书馆里能找到各种“迪伦学家”纯属扯淡的论述,实在没必要再添一本了。但作为《滚石》杂志创刊主编,道尔顿可以回溯到迪伦横空出世的时代,而且他当时就在现场。──《纽约时报》书评
本文由luowang于2021-04-17发表在落网音乐落网记忆落网电台,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lw.oooc.cn/post/2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