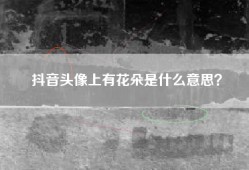靳松:不要等我回来
- 专栏
- 2021-04-17
- 256

打开百度百科,输入“靳松”,首先看到的是:副教授“靳松”。
不是他。
使劲往下拉,出现一段很短的文字:歌手靳松。生于云南丽江,父母是三线建设支边的东北人。童年在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等地的东北人居住较多的林业局小镇里度过。1992年赴昆读书,开始学吉他。1997年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琴,之后漂泊各地。2008年春,录制Demo专辑《不要等我回来》。
网上,靳松的资料少得可怜,寥寥数语又大多一样。
靳松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可音乐又推着他走向人前,从此,喜乐忧愁无从躲避。
“以前只想觅知音,而不是粉丝。现在好些了,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听到你,才有可能有更多懂你的人。”生活永远是你去适应它,不是它来迎合你,靳松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步一步,他被生活拖着走,有时候走太快,会扯得他生疼,有时候走太慢,日子倒也云淡风轻。
与大多数独立音乐人一样,靳松没有签唱片公司的理由是“渴望自由”。“引用别人的话:自由就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他又淡淡地补充了一句:“就是走自己的路。”
靳松在丽江开了一家叫“游牧民谣”的小酒吧,每天傍晚,当丽江褪去白日的喧嚣披上灯红酒绿的夜纱,小酒吧便静静地打开门,它就是靳松在丽江的小屋。靳松有时会和天南海北的朋友聚聚聊聊天,有时仅是蜷在这里,看过往的游客。丽江的生活缓慢倦怠,呆久了的靳松偶尔会感到恍惚,他怕自己这种生活状态会变成一块海绵,放久了,便吸走自由和追求。
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地方,如果不出去走走,靳松总是觉得不安。他曾说过“自己长大后喜欢自由”,自由在当时靳松的意识里又不自觉与流浪划在一起,于是2002年,他选择流浪生活。
靳松小时候频繁转学,新同学熟了就分别,父母带着他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饶了整整一圈。流浪对他来说,和旅行差不多,只是口袋没钱,要靠逃票、卖唱来养活自己。
长期的流浪给了靳松一大票朋友、一小段美好的回忆和切切实实的艰苦体验。
“我们经常说做音乐太苦,其实没什么,还能饿死吗?”经历过流浪生活的靳松,再回头看自己,觉得苦已经不是苦,而是发酵之后微微带点儿自由的甜。

青春始于躁动,终于现实
靳松出生在云南。那里山是真的山,水是真的水。
他的妈妈有一个复音口琴,很老的那种,上海牌。小时候,每天放学,靳松就会爬上学校后面的小山坡,迎风吹一段,当时觉得特有感觉,特潇洒。后来他喜欢看西部片,渐渐发现里面牛仔拔枪之前,配乐都是口琴的呜咽声,特迷人,“是十孔口琴出来的,我马上就去买来吹了”。
吹着吹着,童年就过了,进入青春期的靳松也叛逆躁动。一开始,他用踢足球的方式来释放怒张的荷尔蒙,后来他发现,除了一身臭汗,人静不下来。他想,心灵和情感需要表达呀,该安静地做点什么,于是,他拿起了吉他,这一拿,一辈子便再也放不下。
初学吉他的靳松,在云南封闭的山沟沟里,环境资讯都十分闭塞。“我一直自学,自己扒带,但经常扒错。”那时学校里所谓的高手,也只是搞个简单的弹唱,没有繁琐的效果、复杂的编曲。靳松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弹唱,他想寻找的是一种丰富的感觉,可那时他能接触到的音乐杂志也只有《音像世界》和《音乐天堂》。当从杂志上看到迷笛招生,怀着一腔青春热血,靳松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的音乐旅途。那一年是1997年。
靳松没有念大学,念了三年中专,直接就奔到北京学吉他。“我认识的很多孩子本来是在街上混的,但是后来都成为了很优秀的吉他手。”他口中这样说着,却又在别人谈论起大学生活时候,露出羡慕的神色。其实靳松小时候喜欢的是美术,梦想也是考美院:“前几年全国巡演,每到一处,我就去当地美院看一看,后来认识了很多美院毕业的朋友,其中竟然也有改行从事音乐的,我就想,是不是命中注定呢?我还是会选择音乐吧。”
一直唱歌的靳松,现在也没有放弃画画。他想画画了,就会随便找张A4纸来画,没有原因,就是想画,有时画完也不知道丢哪儿了。“无所谓放弃和坚持,所以对我来说都没那么难,就是听心怎么说,现在会拿手机拍张照片,或传到微博上和大家分享,没有别的意义。”
音乐选择了靳松,同时又结结实实给了他一下子。在国内做民谣,是饿不死人,可他也会考虑到买房买车、养家糊口,最好生活还能更优越体面。“看过1942吗?人的需求超级有弹性的,可高到天低入地下。”
靳松从不否认自己喜欢物质,但他是一个商业头脑极不发达的人,没有什么经商赚钱的本领,他不愿失去珍惜的东西去换取所谓的物质。“重要的是做自己,满足日常生活,其他随缘。”他更看重精神满足,在他看来,物质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本来就是精神上的,何必费劲让自己陷入困惑。
当一切了然于心,靳松的青春就真的过了。哗啦啦的现实潮水般涌向他,唯有闷着头闭着眼,赤裸双脚趟着尖锐的石子过去,才能知道等在对岸的究竟是什么。

一路走一路歌
1998年秋,靳松离开北京跑到更远的东北,组了一个名字很有东北乡村味儿、叫“优质大豆”的乐队。乐队成员在乡下租了个院子,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的东北,呵出一口气都带冰碴。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自己上山砍柴过冬,下雪的时候就在房子里表演自创的小品。
天太冷了,手指僵硬到弹不了吉他,屋子里一副国际象棋和从邻居那借来的麻将,是他们偶尔用来打发寒冷的必需品。“当时觉得很苦,快撑不下去了,现在想想却是挺有意思的。”
靳松前前后后在东北呆了三年,凛冽的气候和温暖的人心形成的强烈反差不断冲击他,让他能够从容地享受苦中作乐。
靳松也曾有过“正经”的生活。在昆明,他像所有普通青年一样,上下班,关注楼盘价格,关注汽车品牌。某天下班,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到酒吧找他的歌手朋友,当时酒吧一个客人也没有,他的朋友抱着吉他,闭着眼睛弹唱一首不知名的小曲,深深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当时内心瞬间被震动,低头看看自己已经变成什么样子,转身就走了。”回去后的靳松立马开始收拾行李,背上吉他离开了昆明。
“我曾留在一个和我格格不入的城市里。”回首过往,内心无法平静的靳松,写下了《不要等我回来》。
2002年,他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流浪生活。这一年,他决定不再做乐队。沉浸在理想主义中的他,带着金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执念,来到广东。南方的冬天不下雪,但冷的刺骨。他的一个朋友,白天教别人弹琴,晚上搭摩的到很远的地方唱上两个小时,为了赚80元。“他也画画,画狗画晾衣架画滴水的衣服。”所有的画组在一起,靳松只看到两个字:生活。
后来他送靳松去外地工作,临行前送给靳松一句话:“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正常的。”靳松一个人想了很久,转身背上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之后,靳松又回到北京,在他眼中,每个年代的北京都有着不同的味道。“我初到北京时住在上地,体院旁边,那时放眼全是菜地和村子。”有的朋友从城市来,居然会闭眼陶醉说:“啊,你们快闻,一股粪香啊?”
北京是所有音乐人的梦,又是最残酷的现实,压力摆在表面,一触即发。靳松不会觉得在北京很累,他有朋友,大家在小屋唱歌,喝酒,抽烟,噜串,聊女人。“吃饱穿暖有地儿住,还好。” 偶尔只剩自己,他也孤单, “孤单每个人都有,我面对它的时候就索性享受它,做些一个人该做的事。”有时他会在公园、地铁或大悦城里呆着,观察人们的生活,“这感觉挺好的。”
靳松的歌大部分都是流浪期间写的,不知是否和流浪有关,他的歌总有一种抹不开的忧郁。靳松乐了:“忧郁?我当然不想忧郁,我希望快乐,希望身边的人都快乐。”
所以,说流浪很苦,他不同意。他一路走着,把自己见到的写下来,想到的唱出来。生活,原本就没那么复杂。

民谣在心中
今年8月8日,靳松在两年没有巡演之后,终于要巡演了。
他微微有点小兴奋:“我很珍惜每一次和观众见面的机会,所以这次专门做了准备,列歌单,买效果器,选吉他。”他甚至买了一个新行李箱。
与此同时,他的新专辑也在筹备中,新专辑不再单单是简单纯朴的民谣,会融入一点其他的元素。“巡演也会唱几首新歌,前两张专辑很多朋友都还没听过呢。”
“你会担心遇到只来不到50人的现场吗?”我问靳松。
“民谣的风格决定了现场不可能像其他音乐那样的音效和火爆气氛,来多少人随缘吧,我见过一个歌手在广阔的场地里对着寥寥几人唱歌,依然很认真很投入很迷人,这个歌手叫陈升。”他看起来并不担心。
提到民谣,靳松话很多。
他喜欢不同风格的音乐,但因个人经历,民谣和摇滚对他影响最大。“在我到处流浪的时候,要靠一把吉他谋生,我不会也不想唱烂大街的流行歌,我就折中一下,去咖啡厅唱国外的民谣歌曲,这样一把吉他和口琴就可以做到了。”遇到其他风格的歌,他也只用这两件乐器演绎,他喜欢的歌都有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去除华丽的伴奏,只用一把木吉他也能弹得好听。
靳松写歌,比较随性。自己在酒吧或和朋友在一起闲聊时,手里如果有吉他,他就会即兴瞎唱一番,自己想不到的词和曲呼啦啦全蹦出来。“朋友都比较喜欢,但是我记不住,唱完就忘,朋友建议我当时要录下来,搞笑的是,录音器一开我就没感觉了。”
一直以来,做民谣甚至做音乐,对他来说都谈不上坚持。他讨厌刻意,认为一切随心就好,他写歌,说白了是为了满足自己。“如果我要选择当一个商业歌手,就不会写现在这样的歌,过现在的生活了。” 他要先探索内心和世界,再然后才是写歌,“当然我和大家都喜欢就更好了。”
靳松很矛盾。不在乎物质又离不开,不世俗却希望大家喜欢。可如果有人不理解他的音乐,他反而不会失望。“我觉得很正常,人和人的需求是不同的,民谣当下尴尬的是真正代表了哪些民众?其实都是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你上街随便找个劳苦大众的一员问问,他不知道什么民谣歌手,但他知道《爱情买卖》。”
认清了民谣大环境的靳松,将民谣放在心底,而他看起来也真不一样了。这几年,他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路也不再那么窄。
至于以后,他没想那么多:“做好每天就好了。”
“那现在的你是真的自由了吧”在采访结束时候,我问靳松。
“我又失去了什么吗?”他反问道。
什么都没失去,什么也没得到。其实,巡演也是一种流浪,而靳松的生活,也才刚刚开始。
本文由luowang于2021-04-17发表在落网音乐落网记忆落网电台,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lw.oooc.cn/post/19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