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莫言:弃婴(上)
- 文学
- 2022-12-04
- 32

弃婴我把她从葵花地里刚刚抱起来时,心里锁着满盈盈的黏稠的黑血,因此我的心很重很沉,像冰凉的石头一样下坠着,因此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灰白的,如同寒风扫荡过的街道。后来是她的青蛙呜叫般的响亮哭声把我从迷惘中唤醒。我不知道是该感谢她还是该恨她,更不知道我是干了一件好事还是干了一件坏事。我那时惊惧地看着她香瓜般扁长的、布满皱纹的、浅黄色的脸,看着她眼窝里汪着的两滴浅绿色的泪水和她那无牙的洞穴般的嘴——从这里冒出来的哭声又潮湿又阴冷,心里的血又全部压缩到四肢和头颅。我的双臂似乎托不动这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裹着的婴孩。
我抱着她踉踉跄跄、戚戚怆怆地从葵花地里钻出来。团扇般的葵花叶片嚓嚓地响着,粗硬的葵花叶茎上的白色细毛摩擦着我的胳膊和脸颊。出了葵花地我就出了一身汗,被葵花茎叶锯割过的地方鲜红地凸起鞭打过似的印痕。好像,好像被毒虫蜇过般痛楚。更深刻的痛楚是在心里。明亮的阳光下,包裹婴孩的红绸子像一团熊熊的火,烫着我的眼,烫着我的心,烫得我的心里结了白色的薄冰。正是正午,田野空旷,道路灰白,路边繁茂的野草,蛇与蚯蚓般地缠贴着。西风凉爽,阳光强烈,不知道该喊冷还是该喊热,反正是个标准的秋日的正午,反正村民们都躲在村庄里没出来。路两边杂种着大豆、玉米、高粱、葵花、红薯、棉花、芝麻,葵花正盛开,黄花连缀成一片黄云,浮在遍野青翠之中。淡淡的花香里,只有几只赭红的野蜂子在飞,蝈蝈躲在叶下,忧郁地尖声鸣叫,蚂蚱在飞,燕子在捕食。悬挂在田野上空、低矮弯曲的电话线上,蹲着一排排休憩的家燕。它们缩着颈,一定在注视着平滑地流淌在绿色原野上的灰色河流。我闻到了一股浓郁得像生蜂蜜般黏稠的生命的气味。万物蓬勃向上,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生动表现是猖獗的野草和茁壮的稼禾间升腾着燠热的水气。天蓝得令人吃惊,天上孤独地停泊着白云像纯情的少女。她还是哭,好像受了巨大的委屈。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个被抛弃的女婴。我的廉价的怜悯施加到她身上,对她来说未必就是多大的恩泽,对我来说却是极度的痛苦了。现在我还在想,好心不得好报可能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你以为是在水深火热中救人,别人还以为你是在图财害命呢!我想我从此以后是再也不干好事了。当然我也不干坏事。这个小女婴折磨得我好苦,这从我把她在葵花地里抱出来时就感觉到了。
破烂不堪的公共汽车把我一个孤零零的乘客送到那三棵柳树下,是我从葵花地里捡出女婴前半个小时的事。坐在车上时,我确实是充分体验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车上那个面如雀蛋的女售票员也是这么说。她可能是头天夜里跟男朋友玩耍时误了觉,从坐上车时她就哈欠连天,而且打过一个哈欠就掉转那颗令人敬爱的头颅,怒气冲冲地瞪我一眼,好像我刚往她的胸膛上吐过一口痰似的,好像我刚往她的雪花膏瓶子里掺了石灰似的。我恍然觉得她的眼球上也生满了褐色雀斑,而她的一次次对我怒目而视,已经把那些雀斑像铁砂子般扫射到我的脸上。我惶恐,觉得好像挺对不起她的,因此她每次看我时我都用最真诚的笑脸迎着她。后来她原谅我。我听到她说:“成了你的专车啦!”我的车长达十米,二十块玻璃破了十七块,座位上的黑革面像泡涨的大饼一样翻卷着。所有的铁器官上都遍被着红锈的专车浑身哆嗦着向前飞驰,沿着狭窄的土路,把路两边绿色的庄稼抹在车后。我的专车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军舰。我的司机不回头,问我:“在哪儿当兵?”“在××。”我受宠若惊地回答。“是要塞的吗?”“是啊是啊!”我不是“要塞”的,但我知道撒谎有好处——有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传染了我。司机情绪立刻高了,虽然他没回头,我也就看到了他亲切的脸。我无疑勾起了他许多回忆,他的兵涯回忆。我附和着他,陪着他大骂“要塞”那个流氓成性的、面如猿猴的副参谋长。他说他有一次为副参谋长开车,副参谋长与三十八团团长的老婆坐在后排。从镜子里,他看到副参谋长把手伸到团长老婆的奶子上,他龇牙咧嘴地把方向盘一打,吉普车一头撞到一棵树上……他哈哈地笑着。我也哈哈地笑着。我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副参谋长也是人嘛!”“回来后就让我写检查。我就写:‘我看到首长在摸女人奶子,走了神,撞了车,犯了错误。’检查送上去,我们指导员在脑勺子上给了我一巴掌,骂我:‘操你妈!哪有你这样写检查的,回去重写吧!’”“你重写了吗?”“写个席!是指导员替我写的,我抄了一遍。”我说:“你们指导员对你蛮好。”“好个屙!我白送了他十斤棉花!”“人无完人嘛!再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了嘛,是‘四人帮’的罪过。”“这些年部队怎么样?”“挺好,挺好。”
车到“三棵树”,我的售票员小姐拉开车门,恨不得一脚把我踹到车下去,但我和司机攀上了“战友”,所以不怕她。我把一盒“9·9”牌香烟扔到驾驶台上。这盒烟劲儿挺大,司机把车开出老远还为我鸣笛致谢呢。
下车。前行。肩背一包糖,手提一箱酒。我必须顶着太阳走完这十五里不通汽车的乡间土路,去见我的爹娘与妻女。我远远地就看到那片葵花地了。我是直奔葵花地而去的。我是在柳树上看到那张纸条后跑向葵花地的。我是看到了纸条上写的字就飞跑到葵花地里去的。
纸条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速到葵花地里救人!!!
那片葵花地顿时就变得非常遥远,像一块漂游在大地上的云朵,黄色的、温柔的、馨香扑鼻的诱惑强烈地召唤着我。我扔掉手提肩背的物件,飞跑。在焦灼的奔波中,我难忘的一件往事涌上心头。那是前年的暑假,我回家的路上,由一条白狗为引,邂逅了久别的朋友暖姑,生出了一串故事。这些故事被我改头换面之后,写成了一篇名为《自狗秋千架》的小说。这篇小说我至今认为是我的好小说。每次探家总有对故乡的崭新的发现,总有对过去认识的否定。纷繁多彩的农村生活像一部浩瀚的巨著,要读完它、读懂它并非易事,由此我也想到了文人的无聊和浅薄。这一次,又有什么稀奇事儿等待着我去发现呢?根据柳树上纸条的启示,用某学院文人们的口头禅说,这一次的节目将“更加激烈,更加残酷”。葵花,黄色的葵花地,是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幽会的地方,是一片引人发痴的风流温暖的乐园。我跑到它跟前时,已经出气不迭。粗糙的葵花叶片在温存的西风吹拂下拉拉响着,油铃子、蟋蟀、蝈蝈欢快又凄凉地叫着,后来给我带来无数麻烦的女婴响亮地哭着。她的哭声是葵花地音响中的主调,节奏急促、紧张,如同火烧眉毛。
我从没有看到过成片的葵花。我看惯了的是篱笆边、院墙边上稀疏种着的葵花,它们高大、孤独,给人以欺凌者的感觉。成片的葵花温柔、亲密、互相扶持着,像一个爱情荡漾的温暖的海洋。故乡的葵花由零散种植发展到成片种植,是农村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生动体现。几天之后,我更加尖刻地意识到,被抛弃在美丽葵花地里的女婴,竟是一个集中着诸多矛盾的扔了不对,不扔也不对的怪物。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张白纸那么薄;人性,其实也像一张白纸那样单薄脆弱,稍稍一捅就破了。
葵花茎秆粗牡,灰绿色,下半截的叶子脱落了,依稀可辨脱叶留下的疤痕,愈往上,叶片茂盛得愈不透光。叶色黑绿,不光滑。碗大的无数花盘挑在柔软的弯颈上,像无数颗谦恭的头颅。我循声钻进葵花地,金子般的花粉雨点般落下,落在我的头发上和手臂上,落进我的眼睛里,落在被雨水拍打得平坦如砥的土地上,落在包裹婴孩的红绸子上,落在婴孩身旁三个宝塔状的蚁巢旁边。熙熙攘攘的黑色蚂蚁正在加紧构筑着它们的堡垒。我猛然感到一阵蚀骨的绝望,蚂蚁们的辛苦劳动除了为人类提供一点气象的信息外,其实毫无价值。在如注的雨水下,高大的蚁巢连半分钟也难以支撑。人类在宇宙上的位置,比蚂蚁能优越多少呢?到处都是恐怖,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欺骗、谎言、尔虞我诈,连葵花地里都藏匿着红色的婴孩。我是有过扔掉她走我的路的想法的,但我无法做到。婴孩像焊接在了我的胳膊上。我心里好几次做出了扔的决定,但胳膊不听我的指挥。
我回到三棵树下,再一次研究那纸条上的字。字们狰狞地看着我。田野照旧空旷,苟延残喘的秋蝉在柳树上凄凉地哀鸣,通县城的弯曲的土地上泛着扎眼的黄光。一条癞皮的、被逐出家门的野猫从玉米林里钻出来,望了我一眼,叫了一声,懒洋洋地钻到芝麻地里去了。我看了看婴孩肿胀透明的嘴唇,背起包,提起箱,托着婴孩,往我的家中走。
家里的人对我的突然出现感到惊喜,但对我怀抱的婴孩则感到惊讶了。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站立不稳的身体表示他们的惊讶,妻子用她陡然下垂的双臂表示她的惊讶,惟有我的五岁的小女儿对这个婴孩表示出极度的兴奋。她高叫着:“小弟弟,小弟弟,爸爸捡回来一个小弟弟!”
我自然知道女儿对“小弟弟”的强烈兴趣是父母和妻子长期训练的结果。我每次回家,女儿就缠着我要小弟弟,而且是要两个。每逢这时,我就感觉到父亲、母亲、妻子,用他们严肃的、温柔的、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对我进行严厉的审判。有一次,我惶恐地把一个粉红色的塑料男孩从旅行包里摸出来。递给吵嚷着要小弟弟的女儿。女儿接过男孩,在孩子头上拍了一巴掌,男孩头嘭一声响。女儿把男孩扔在地上,哇一声哭了。她哭着说:“我不要,这是个死的……我要个会说话的小弟弟……”我捡起塑料男孩,看着他过分凸出的大眼睛里泛动着的超人的讥讽表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父亲和母亲各叹了一口气,我抬起头来,看着妻子黑漆般的脸上,两道浑黄的泪水流成了河。
家里人除女儿外,都用麻木的目光盯着我,我也麻木地盯着他们。我自我解脱般的苦笑一声,他们也跟着我苦笑,无声,只能看见他们泥偶般的脸上僵硬的、流质般的表情。
“爸爸!我看看小弟弟!”女儿在我面前蹦着喊叫。
我向他们说:“捡的,在葵花地里……”
妻子愤怒地说:“我能生!”
我蔫头蔫脑地说:“孩子她娘,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母亲说:“救得好!救得好!”
父亲始终不说话。
我把婴孩放在炕上,婴孩抽搐着脸哭。
我说她饿了。妻子瞪我一眼。
母亲说:“解开看看是个什么孩子。”
父亲冷笑一声,蹲在地上,掏出烟袋,巴嗒巴嗒抽起烟来。
妻子匆匆走上前去,解开拦腰捆住红绸的布条,抖开红绸,只看了一眼,就懊丧地退到一边去。
“看小弟弟!看小弟弟!”女儿挤上前来,手把着炕沿要上炕。
妻子弯下腰,对准女儿的屁股,凶狠地抓了一把。女儿尖叫一声,飞快地逃到院子里,撕着嗓子哭。
是个女婴。她蹬着沾满血污的、皱皮的小腿嚎哭。她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哭声洪亮,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孩子。她的屁股下有一大摊黑色的屎,我知道这是“胎粪”。在红绸子上像软体动物一样蠕动着的是个初生的婴孩。
“丫头子!”母亲说。
“不是丫头子谁家割舍得扔!”父亲把烟袋锅子用力往地上磕着,阴森森地说着。
女儿在院子里哭着,好像唱歌一样。
妻子说:“你从哪里抱来的,还给人家抱回哪里去!”
我说:“抱回去不是明明送她死嘛!这是条人命,你别逼着我去犯罪。”
母亲说:“先养着吧,先养着,打听打听看有没有缺孩子的。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你们行了这个善,下一胎一定能生个男孩。”
母亲,不,全家人,念念不忘的就是要我和妻子交配生子,完成我作为儿子和丈夫的责任。这种要求的强烈程度随着我和妻子年龄的增大而增大,已临近爆发的边缘。这种毒汁般的欲念,毒害着家里人的情绪;每个人都用秤钩般的眼睛撕扯着我的灵魂。我多次想到缴械投降,但终究没有投降。现在,每逢我在大街上行走时,我就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恐怖。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抑或外星球上降落下来的人形怪物。我酸苦地瞅一眼无限虔诚地为我祝祷着的母亲,连叹息的力量也没有了。
我找出半卷手纸,为女婴擦拭胎屎。成群结队的苍蝇嗅味而来,它们从厕所里飞出来,从猪圈里飞出来,从牛棚里飞出来。汇成一股黑色的浊流,在房间里飞动。炕下的暗影里,成群的跳蚤像子弹般射来射去。胎粪又黏又滞,像化开的沥青,像熬熟的膏药,腥和臭都出类拔萃。我吃力地擦着胎粪,微微有点恶心。
妻子在外屋里说:“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好像不是你的种,人家孩子你擦屎擦尿,好像是你亲生的。没准就是你亲生的,没准就是你在外边搭伙了一个大嫚,生了这么个小嫚……”
妻子的语言搀和在嗡嗡呜叫的苍蝇的漩涡里,把我的脑浆子都给搅澥了。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够了!先生!”
她不说话了。我盯着她因为愤怒惊惧变成了多边形的脸,听到我的女儿在胡同里与邻居家的女孩嬉闹着。女孩,女孩,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女孩。
尽管小心翼翼,胎粪还是沾到了我的手上。我感到这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能为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女婴擦拭她一生中第一泡屎,我认为是我的光荣。我索性用手去擦、用弯曲的手指去刮黏在女婴屁股上的黑便。我斜目看到妻子惊愕得半张开的嘴,突然爆发了一种对全人类的刻骨的仇恨。当然我更仇恨我自己。
妻子前来帮忙。我不对她表示欢迎也不对她表示反对。她走上前来,熟练地整理襁褓;我机械地退到后面,舀一点水,洗着手上的粪便。
我听到妻子喊:“钱!”
我提着手站起来,看到妻子左手捏着一方剥开的红纸,右手捏着一把破烂的钱票。妻子扔下红纸,吐着唾沫,数着手里的钱。她数了两遍,肯定地说:“二十一块!”
我发现她的脸上生出一些慈祥的表情。我说:“你把莎莎小时用过的奶瓶拿出来涮涮,冲些奶粉喂她。”
“你真要养着她?”妻子问。
“那是以后的事,先别饿死她。”我说。
“家里没有奶粉!”
“你到供销社买去!”我从衣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她。
“不能用咱们的钱,”她晃晃手中那沓肮脏的钱票,说,“用她自己的钱买。”
一只蟋蟀从潮湿的墙角上蹦起来,跳上炕沿,在红绸子上弯弯曲曲地爬动。蟋蟀咖啡色的肉体伏在深红的绸子上,显得极端严肃。我看到它的触须神经质地颤抖着。女婴从襁褓中挣扎出一只大手,举到嘴边吮着,那只手巴骨上裂着一些白色的皮。女婴一头乌发,两扇耳朵很大,半透明。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和母亲也站在了我的身后,看着饥饿的女婴啃食拳头。
“她饿了。”母亲说。
“人什么都要学,就是吃不用学。”父亲说。
我回头看着两位老人,心里涌起一股滚热的浪潮。他们像参拜圣灵一样,与我一起,瞻仰着这个也许能成为盖世英杰的女婴布满血污的面孔。
妻子买回来两袋奶粉,一袋洗衣粉。我亲自动手,冲了一瓶奶,把那个被我女儿咬烂了的乳胶奶头塞到女婴嘴里。女婴晃了几下头,便敏捷地咬住了奶头,紧接着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响。
吃完一瓶奶,她睁开了眼睛。两只黑蝌蚪般的眼睛。她努力看着我,目光冷漠。
我说:“她在看我。”
母亲说:“初生的孩子,什么也看不到。”
父亲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怎么知道她什么也看不到?她打电话跟你说啦?”
母亲退着走,说:“我不跟你抬扛,她能看到,看不到,都随她的便去。”
女儿从胡同里跑回来,高声喊叫着:“娘,打雷了,上来雨啦。”
果然,站在房子里,就听到了西北方向持续滚过推磨般的雷声。通过捅破纸的后窗棂,我看到了那半边天上毛茸茸的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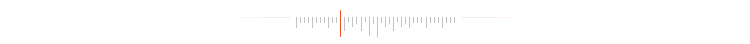
精彩专辑
《九州作家》综合专辑
小说专辑
名家名篇
歌词专辑
散文专辑
诗词专辑
杂文专辑
莫言专辑
贾平凹专辑
九州微小说
验方精选
菜谱食谱
百首绝句专辑
《九州作家》小说连载专辑
王福林《河魂》小说连载
短篇小说《父亲的心愿》
长篇小说《世纪初的情恋》
少儿长篇小说《啊,我的桑椹园》
少儿长篇小说《菊花樱桃红》
电影剧本《秦朝明将蒙恬传奇》
中篇小说《乡村魂》
长篇小说《归来的战俘》
短篇小说连载《赵老大家的喜事》
中篇小说《初恋》
中篇小说《血色浮情》
长篇小说《新红日》
中篇小说《口蹄疫》
纪实文学《黑土地》
梦幻小说《我于前天去世》
长篇小说《编外的忠诚》
小说连载《我心里的女人们》
中篇小说《关 山 逃 情》
长篇小说《潮白小八路》
中篇小说《济川王之后》
中篇小说《与老鼠决斗》
小说连载 《魔遇》
精彩榜
1.《〈九州作家〉会员专辑》及《2020年往期精彩榜》
2.《〈九州作家〉专辑》及《2021年往期精彩榜》
▲滑动方框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本文由落网记忆APP于2022-12-04发表在落网音乐落网记忆落网电台,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lw.oooc.cn/post/46815.html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