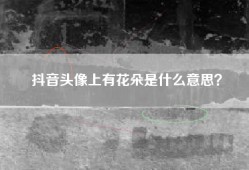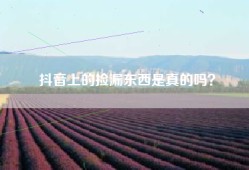在路上
- 专栏
- 2021-04-17
- 188
聪聪告诉我他今年高考考砸了。家里的人和身边的朋友都在打探他的成绩,他说他这一次让所有人失望了,感觉他爸妈都哭了,只是没有在他面前。
聪聪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没比我小多少,但按照辈分却要叫我小姑。我们见过一次,在我坚决要休学旅行的那年。那时候明明没什么的我却成了他在高中那几年日日提起的偶像,我一开始欣然接受了,到后来却是逃避着推脱责任。因为姥姥总是小心翼翼和我说:“唉,听你婶儿说,聪聪最近成绩下降了……”
一开始我并不明白这话里是什么意思,一直到有一天老妈突然倚在我房间门口问我:“你最近还和聪聪联系吗?”我如实说联系得很少,因为那时候我只急着说服老妈让我去印度,然后好去找苏扬,根本没心思去搭理别人的事情。“嗯,你就少跟他联系。他天天跟他爸妈说你一个人去西藏徒步墨脱什么的,他现在成绩一退步,别人肯定都觉得是你影响的。”我不爽地回答:“关我什么事,我又没让他休学跟我一块玩。”
老妈说完这话便也就转身回屋了,那时候我们之间也闹别扭。我每天在家嚷嚷着要休学然后立马回西藏,再从尼泊尔去印度,最后再坐船去埃及。我没明说苏扬的事,我也以为他们不知道。我经常晚饭后坐在客厅等待着和晚归的父亲谈心,一开始尝试走心理战但往往自己说着说着就开始哭然后开始耍无赖。我爸最见不得我哭,不是那种心软的见不得,而是烦。我们就慢慢在客厅里抬高音量,我一边哭闹一边斩钉截铁地对我爸说:“你必须让我走。”他不搭理我,也不说话,只是拿着遥控器对着电视不停的换台,眉头都快能皱在一起再打一个结。每一次的对话都是以我摔门回屋结束,或者偶尔老妈加入最后的吵架阶段,最后我再摔门结束。
我和他们说,我在西藏的一个多月好好地思考了我的人生,要他们尊重我的决定。我说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庸庸碌碌地渡过一生,我说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有一次我爸终于开口和我讲话,他说他曾经也有一个梦想,他说他曾希望有一天,把家里的房子卖了,然后买一辆房车,带上我跟我妈,一边走一边打点零工。他说这个的时候笑得满脸皱纹,他问我:“我觉得我们三个一起,还是能养活住自己的吧?”但他说起这话的时候,更像是一个肯定句。
我记得那天我情绪有点激动,因为苏扬已经到印度好几天了,而我这儿还没一点动静。我反问我爸,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然后他笑了,我觉得那笑里带了点自嘲的味道,他说:“世界上有一亿人想成为居里夫人,但成功的有几个?”那时候我只顾着自己好不容易看见的曙光幻灭的悲伤,却根本没仔细去看看他那时候的表情。我愤怒地往房间走,我一边走一边说:
“我要是不试试,我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几个成功的人之一呢?”然后一切谈话还是被我那干脆又沉重的摔门声斩断。我趴在床上痛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也有过曾经这样的梦想却放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过这样梦想的他们却不站出来支持我。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人,好像都疯了。我觉得他们没救了。
“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是来自心底的声音。
就这样又僵持了好久,他们还是会给我做饭,给我零花钱,但是就是不让我走。但其实话说回来,那时候的我也并不是什么为了得到家人允许才在那里墨迹,说到底还是自己兜里没有钱,要管爸妈要。我那时候以为我的梦想是全世界,甚至全宇宙最伟大的梦想。因为它看起来美好,看起来那么单纯。就是想背上背包,一边打工一边体验着这广袤无垠的世界。其实现在看看不过就是那强烈的炫耀欲望和极度的想要证明存在的意义。
而在内心里最能满足自己炫耀欲与存在感的,是因为苏扬的存在。我是在拉萨遇到他的,在我第二次进藏的时候。那时候拉萨大昭寺门口的艳遇墙还允许坐着边喝酥油茶边聊天,那时候拉萨也还没那么多小清新和吹牛逼的,而那时候的墨脱也还不是安妮宝贝小说里的那个。

那天晚上,我和跟我一起徒步墨脱的朋友一起在酒吧喝酒,后来干脆三个人买了一箱拉啤就抱着上青旅的天台去喝。就在那时,我碰见了也在喝酒的苏扬,和他的朋友小涂。对于游客来说,拉萨是个太小的城市。我之前见过苏扬几面,人长得精神又帅,是难得的能令我过目不忘的人。于是五个人就自来熟地坐在一起。
那天大家都喝醉了,不知道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离别近在眼前而徒增了几分伤感,还是是能从陌生人那里得来一份超越普通朋友的信任。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今天我告诉你所有秘密,明天你就忘了我是谁,回到现实生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没什么利益关系,所以谁也没必要掩饰自己什么。不知道是谁先开始讲了心里话,到最后居然成了五个人抱头痛哭的情形。
和我一起徒步墨脱的那哥们儿一直抱着我说,我就是太要强。他对苏扬和小涂说:“你们知道么,我一个星期有四天都在山上待着,但这姑娘徒步经验几乎是零,她居然一直跟着我。最后一天止痛片吃完了,绷带用完了,她脚指甲翘起来了三个,满脚都是血泡,却居然一句话没说,边哭边走了8个小时。一直到我们发现她不对劲的时候,脱下鞋一看,都惊呆了。这姑娘就是太倔太要强了……”我现在还记得那哥们儿说话时的语气,他都哽咽了。
但更令我难忘、令我震惊的是,小涂趁苏扬去下面买酒时,哭着对我们说:“你们看他怎么样?人好吧,也特别有才,但却得了一种可能连30岁都活不过的病。”小涂猛得喝一口酒,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从苏扬身上,我才意识到一件事。人这一辈子,时间是有限的,但我们却可以把宽度扩到无限。”
对于那个时候正在所谓流浪的我,这句话简直是说到了我的心窝,那瞬间巨大的共鸣感让我饱和到觉得那些按步就班生活老去的人都是只剩躯壳的行尸走肉。后来再见到苏扬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非洲,他眼神特别诚恳,我就答应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答应了。我没法定义那种感觉叫做一见钟情,或者什么,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出现了一个人,他的喜好,他的言谈,他的观念都深深地填满了你心里的那些缝隙。除此之外,他的存在,也填满了一个少女心里的全部虚荣——一个看了太多韩剧而以为只有车祸失忆治不好的爱情才伟大的脑残观念。你甚至迫不及待得想和他在一起,然后告诉全世界你有一个身患绝症的男朋友,并且你决定陪他一起环游世界知道他生命尽头。而你所想做的这一切根本只是想用来彰显你的伟大。
人有时候是多么可笑,做那些稀奇古怪又可笑的事情却只是想弥补自己的存在感。
在当时那种迷茫、恍惚、却自以为找到人生终极目标的那种状态下,我欣喜得好像找到了上帝藏起来的那颗糖果。但其实我那时候想到的是:嘿,你们看,当你们还困在应试教育的铁笼里时,我已经飞向了天堂。
那是彻头彻尾的显摆,想给自己贴上了不起的标签,而那所谓的人生终极目标就好像是最后的那一根救命稻草。但这都是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现在,我才体会到的。
故事后来,我还是去了印度,却是在和苏扬约好的一年之后。那时候和爸妈的那场较劲,最后看起来好像是我赢了。我妈和我一起飞去了拉萨,她说那里真的有让人心静的魔力。只是我并没有像原计划那样,从拉萨去尼泊尔,然后去印度找苏扬,因为苏扬也没有像原计划那样坐船去埃及。他有事要回新加坡,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这一次我拒绝了,我从来没有跟他解释过原因,他也没有多问些什么,只是突然间断了联系。
那时候我试着选择一条最不会吃亏的路给自己。我想,答应一起去南非是觉得,就算两个人以后分开,至少也还完成了一个梦想;如果和他回了新加坡,有一天被甩了的话,那放弃一切只为他奔赴过去的我,岂不是看起来很傻?所以我心存犹豫却也还是拒绝了他的邀请。我当时为自己的那点小聪明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了明智的决定。但后来,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没勇气抓住幸福的人是多么深入骨髓的悲哀。就这样,他变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在心里根深蒂固。
但事情总有超乎你想象的那一面,就比如说一直到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跟苏扬两个人的感情都是认真的。只是两个患得患失的人,注定是不会在那时候成为上帝的宠儿。当我终于想明白也愿意放下一切的时候,却再也没有当时的机会了。我突然想起了曾经在我拒绝和他回新加坡后他说过的那三个字。
“忘了吧。”

后来我追逐着他的足迹去了很多地方,但最终都是晚了一步。我试着安慰自己,说可能在那个平行世界里,我们是在一起的。但自欺欺人,和这种毫无建设性的自我安慰,都在现实面前显得异常脆弱和牵强。你活着,你就会一直被提醒,提醒着你的渺小,以及无能为力。
在休学一年半之后,我重返了学校,但这一次却是明明白白的在那教室里坐着。
“你为什么要选择学生化?”
“我想在大学毕业之后考进医学院然后成为一名医生。”
“你为什么想成为医生?”
“我不想再看到我身边的人失其所爱。”
而我知道,聪聪正在经历这一个阶段。曾经我们都被家人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在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那一刻,最愧疚的不是对自己,而是对那份长年来的信任。 但我知道,当有一天我们终于无法再逃避生活,终于能够直面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那些年彷徨过、蹉跎过的时光,都是值得的。我没办法给他直接的建议,告诉他,现在要如何安抚家人,或到底应该选什么专业。但我只是告诉他了一件事,相信自己,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生有时候要多迷一些点路,多撞见一些人,才能发现那个发着耀眼光芒的人生指路牌。
梦想一直在前方,我们一直在路上。
本文由luowang于2021-04-17发表在落网音乐落网记忆落网电台,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lw.oooc.cn/post/19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