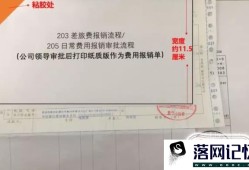土地里生长的野孩子——【时代的自由之声】
- 专栏
- 2021-04-17
- 216

当我们聆听民谣的时候,我们究竟听到了什么?
像古老的叙事者,背着班卓琴和酒壶,摇摇晃晃走过边陲的村落;像一支小调,莲花似的绽放在姑娘的嘴角,被流浪人采了去,在低吟里嗅一嗅香。音乐的形式和载体变了,语言也在更迭的乐器和文字间辗转,只有自由融进民谣的血脉,血一样浓稠或稀薄,血一样没有形状,血一样流淌。
如今,万总哄女儿似地唱着成年人温吞吞的童话,让世事都围着一个陀螺转;逼哥自说自话,人生观也和琴弦一起拧紧了;尹吾揣着北岛的诗,却活在余华的故事里;宋胖子的忧愁大概只因为姑娘和地名吧,小河变着法儿地玩耍,周云蓬走失在旧州调子和水墨卷帙,甚至老狼的蓝色理想也是过了气的自由…
不,这些都不是。我想让你听听野孩子,听听我和你说的这种民谣、这种不变的自由。
其实我想避免谈论自由。观念中自由消逝在对自由的辩解中,消逝在对自由的追求中。我们对于自由的界定已经给自由框定了范畴:辞职搭车旅行、与传统观念对立、背弃既成的社会体制、骄傲地扛着四面为敌的大旗……但这真的是自由吗?当你赌气似的享受和炫耀这种敌对,当对峙成为不负责任和不切实际的缘由,自由是借口还是标签,是主张还是逃避?它还是活着的感觉吗?
野孩子乐队似乎不去想这个。唱民谣的不一定要小众,唱民谣的不一定要流浪,但是唱民谣的一定要排练。他们是朴实的,朴实得有点土气。十几年里十几支歌翻来覆去地排,乐器和人声好像汇聚成了生命体。
张玮玮的手风琴徐徐地一开一合,像老式的火车缓缓地穿过。张佺弹着冬不拉吹着口琴,格外响亮。不过那是各自独奏的时候,当乐声和人声相合,丰富的声场又是那么简单,像一穗叠一穗的庄稼,像斑斓羽毛墨眼珠儿的鸟,精巧、有序、没一点错儿,却自自然然的,生来就是这样。
自由也不是天生的。诅咒自己什么苦难都看不见,唱着生活这首最难唱的歌,最后还是热切地歌唱故乡、远方和心里的执着。怒气和委屈平息了,洞察和宽谅都通透了,现实不够痛快,但歌声能带来痛快,自由也随之而来。像他们歌唱的梵高,疯子不咒骂灰暗的现实,疯子给自己一只盛满太阳的眼睛,疯子是最自由的。

这些都与他们纯朴的本真有关。民歌的传唱本身就是不受拘束的表达,滚烫的汗水和炽热的心被口口相传的调子保留着温度,给这个忽冷忽热的时代一种带着哭腔的热情。黄河边儿的歌谣跟着河水流了太久了,冲刷着泥沙俱下的日子里浑浊的自由,这种自由等待着一个人去走,去看,去低头做事沉淀自己,直到澄得清澈。
这自由里还有顺其自然的放下和执着。北京北京我不能忘记,北京北京我要去哪里。城市之光在夜晚亮起,一块块LED屏上的字体棱角一致,霓虹灯和高架桥的光晕模糊。想起一个夏日清晨,我在海淀桥发了会儿呆。五点钟的北京已经在酝酿奔流的车辆和人群,城市里的人,你们都急着去哪儿?
城市听着河酒吧里整晚整晚的唱,看着他们混出个样子又伤心地离去,北京北京你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北京北京你全都忘记了。可是唱起城市,他们只当歌唱。不提人声鼎沸的快活,张佺不去谈小索逝世的苍凉,张玮玮和郭龙也打磨了最好的时光塞进《白银饭店》,再不玩花样。他们眼里还跃动着光晕,那是日子沸腾和熄灭的总和,那是太阳下山了,月亮也下山了,再自然不过。
听着野孩子,像撒丫子奔跑在广袤的原野,像日子转动的机械声被自然的节奏替代。可还是要不停地跑,还是要不停地劳作,不能停,也不能丢了自己。这是现实中的超现实主义,真正的自由也不过如此。
我喜欢他们现在的状态。像张玮玮说的:“在大理,每天唱歌练琴就是劳动,最幸福的时候是排练完回家,像小学生放学了走在路上一样高兴。”
遍寻自由而无处可得,因自由而日夜焦灼,被自由勒住脖子非调转方向不可,被自由压得喘不过气……你是否还能感觉到这样简单的自由?我难以描述这样的简单。这感觉并不好受,像捧着一碗热乎乎的玉米碴子粥,急急地跑着,却找不到送给你的路。怕它洒了,怕它凉成浆糊,怕你不能就着冷而腻的生活仰头灌下一大口,怕你感觉不着从舌头到胃里暖和的自由。
可野孩子根本不需要什么描述。不要问山高路远我是谁,不要管太阳下面我信谁。他们默不作声,除了歌唱。他们看着自由和音乐、快乐、茄子一起从地里长出来。只要有土地,就生长着自由。
本文由luowang于2021-04-17发表在落网音乐落网记忆落网电台,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lw.oooc.cn/post/19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