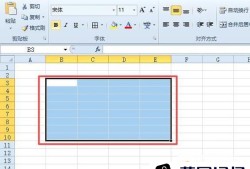闪光的马——【忘记我,记住我之怀念Sparklehorse】
- 专栏
- 2021-04-17
- 204

亲爱的Mark:我一再地想,如何的口吻,如何的开头,如何的称呼,能写一封信给你。
Sparklehorse,闪光的马,火花的马,失真的电声里你跳跃着,迷幻的梦呓里你袒露一只失焦的大眼睛,丰富的留白里你轻巧地停顿,那些明灭的光点一闪一闪。
Sparklehorse,闪马,他们这么叫你。他们说,Mark Linkous是Sparklehorse的灵魂人物,十几年间在轮椅上写了许多的迷幻民谣与氛围电子乐。
不,Sparklehorse,你不是那个“身残志坚”的创作机器。从多年前的偶遇,到这个格外想念你的冬季,你依然是我心中那匹闪着火花的马,在雾气蒙蒙的原野,在阳光碎裂的山坡,伫立或奔跑着。
第一次遇见你,是《Dreamt for Light Years in the Belly of a Mountain》。专辑封面铺展的红裙子旁缀满枯叶和果实,配上不相称的小女孩的石膏塑像脑袋,像秋天一个荒诞的谜语。
谜底呢?我在你的声音里找谜底,找那个穿透暴戾的节奏与黯淡的吟唱的谜底,虚无飘渺的谜底。谜语的答案是死去、流亡和破灭,可是这些晦暗的情绪又被包裹在绚烂和宁静中,像七彩肥皂泡升腾到高空、濒近破灭的一霎,像冰冷的铁器相互碰撞,淬炼出瞬间闪灭的精致火花。Mark,每当我想要描述你的声音,描述纷乱的节奏和明澈的配器,都只能摒弃具象的形容,坠入幻象的美丽。
穿红布裙的小姑娘跑向了女巫的庄园,太阳垂下来掉进山坡旁的湖里。风起了,棉铃、大麻和黑麦连根拔起,飞向半空。风停了,它们带回了已经枯萎的精灵。沼泽倒映你的眼睛,触摸它吧,触摸湖水打湿的云。
Mark,你不仅仅会编织谜语。是药物给了你印象派的瞳孔,还是躁郁症给了你诗人的嘴唇?你的音乐、词语和画面总是相配着带给我梦境。比如《Vivadixiesubmarinetransmissionplot》,长而繁复的单词藏着潮湿的秘密,朦胧的暖色封面上有一张小丑滑稽的笑脸。你可以画一幅迷离的画儿,读一首神经质的长诗,却在崩溃和瘫痪之前,好像预言似的录了这样一张专辑。
It’s sad & beautiful world,你这样唱着,也这样阴郁和美妙。你看见红色以外的红,紫色以外的紫。你记录幼童才能听见的纯洁的尖叫,你眼眶和太阳穴间栖息着一只蝴蝶,你模拟它煽动翅膀的声音。
不,Mark,这样的形容似乎都太虚幻了,仿佛是听着《Homecoming Queen》在浅睡中发出的呓语。在学会将音乐分门别类之后,我试图定义你,用标签来标榜Sparklehorse:独立,噪音,实验,氛围……可是这清醒的界定在圆整的梦境太突兀了。我要剔除它们,Sparklehorse没有沿袭某种演奏风格,你只是永远在拨弄自己的神经。我要回到梦境,节奏和音色被分拣的音乐世界里,没有你所给予的圆整的诡谲与美丽。
最好听的专辑要属《It’s a Wonderful Life》,灌满了一整张唱盘的幻觉,所有的词汇和音符都是金色的。如果一首歌能唤起童年午后穿过的那片鲜绿树林的记忆,又会带来垂死的人眼前的一幕幕幻象,这样的音乐是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还是独立于我们的思维之外?
Mark,我喜欢这些幻觉,仿佛我拥有前世今生一样,仿佛亮眼睛的孩子一样,仿佛死神搀扶的老者一样。如是,随时想要回到这样的幻觉,休息或哭泣,兴奋癫狂或安宁沉静。
悲哀的意识流、致幻品和安慰剂,总是精神的痛苦催化产生了艺术,带来你的不幸与我们的幸运。我学习人脑层层包裹的皮质,记忆五十二个斑斓的脑区,却解不开你怪异的幻觉。我知道颞叶病变的姑娘可以看到红绿灯流动如霞光,海马体损坏的患者会活在永恒的逝去,却不知道如何解释嗑药带给你的绝望与热爱——那不仅仅是药物的作用,一如无法分析我们共有的病态的快乐与尖锐的阴郁。
这些真实的意识和情绪只有借着幻觉传达而共鸣,在精致的大脑中脱离囊体、核团和神经末梢,编织一个叫“灵魂”的异度空间。季风在旋转,星云漂浮,电子前赴后继地爆炸,田园里的墓碑上麻雀在跳舞,机械人的脸颊散发温热,动物的骨头甜美柔软。
那里牵不住一匹闪光的马,它毛皮柔腻,垂下眼皮,向远处奔去。

Sparklehorse,成立于1994年,来自美国维吉尼亚乡村。1996年出版名字冗长的第一张专辑《Vivadixiesubmarinetransmissionplot》,同年,主创Mark Linkous因乱用药物昏迷,长期压迫导致下肢瘫痪,依靠轮椅度过余生。Mark的意外事故使这个几乎未离开乡下的乐队一度屡现媒体报道,Sparklehorse的作品也在独立音乐界倍受青睐,直到2009年,他们还创作了无比压抑的实验化专辑《In the Fishtank 15》。然而,2010年3月7日,Mark对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身亡。
Sparklehorse,我亲爱的闪马,如这世界般温暖、阴暗又奇异的闪马,你奔向了哪里?
这个冬季再听Sparklehorse,在目睹死亡和经历失去后,我更深地理解了曾经那个秋日谜题的答案。但你死了,多年以后,你变成了那个谜底的一部分,死去、流亡和破灭,绚烂又宁静。
我在这个冬天想念你。浓黑的冬夜听《Saint Mary》,我也躺在圣玛丽医院的病床上,和你坠入生死之间的灰色地带。难得的好天气,我把手贴在镀满阳光的墙壁上,摇摆着与你一同唱:I’m so sick of goodbyes。更多的时候,冬日午后弥漫着灰白色,你铺就一张Apple Bed,填满一片Sea of Teeth,我看见温暖的烟,温暖的雾气,温暖的阴云,温暖的灰白色覆盖我的眼睛。
若冬日冷雨乍停,踩着《Hundreds of Sparrows》的节拍迎着一滩血似的夕阳快步地走;若隔窗望飘雪,听《Dreamt for Light Years in the Belly of a Mountain(aka Maxine)》,洁白埋葬荒芜,荒芜吞噬洁白,世上还剩下什么呢?最奇妙的是早晨醒来听《Gold Day》,浸在迷蒙而暖和的睡意。Mark说过,每天早上醒来痛苦的是发现自己还活着。可你如何写得出这样金光闪闪的清晨?Good morning, my child,你唱得那么温柔。
亲爱的Mark,这是一份迟到了太久的怀念。你的音乐有春天花朵盛开的糜烂芬芳,夏日回旋的明亮光晕,秋季猩红色果实的熟烂味道,却在严冬时节让我一再地怀念,一再地追随那匹发光的马儿。这个冬天,我读到那句诗:你惆怅的嘴饮着黑暗/一点一滴/而你的眼帘/还遮护着/为我仅余的蓝天,而你仍在我耳边低吟着:I wish I had/ a horse's head/a tiger's heart/an apple bed……
本文由luowang于2021-04-17发表在落网音乐落网记忆落网电台,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lw.oooc.cn/post/18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