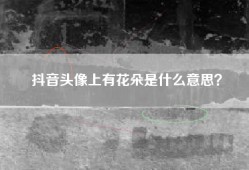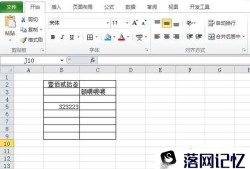崔健:二十多年来
- 专栏
- 2021-04-17
- 182
当我写了《红旗下的蛋》以后,我就厌恶了这种横空出世的位置,我试图把两脚落在地上,这个感觉就像将军开始当兵了,要解决具体问题了。可是很多人并不愿意关注士兵,他们还是愿意服从于一种权威和势力。
—崔健

这是我第四次采访崔健,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很显然,采访崔健远远没有听他的摇滚过瘾,当他在滔滔不绝地试图表达他头脑中的各种想法时,你会发现语言表达和思维上的不连贯让他无法说清楚任何一个问题,就像他的一句歌词描述的那样:“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只是积压已久的一切本能的反应。”这种感性、跳跃性的思维方式常常让他的表述前后矛盾,他自己却浑然不知,这些话要是变成歌词,可能会更精彩一些。
第一次采访崔健是 1996 年,他当时谈得最多的是语言的终极批判问题,他一直反对语言带来的结论。现在,他似乎明白了,很多话用音乐来表达是不够的,他开始像个评论家一样用他当年不屑的语言批判来扩大他音乐的外延力量。很多别人早就搞明白的问题,他今天还看不明白,一直较着劲想弄明白。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较劲让崔健变成了一个有魅力和标志性的摇滚艺术家,但是在今天,这种较劲让他越来越拧巴。甚至,这次采访谈论的很多问题,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都谈过。我发现,崔健多年来的特殊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与人交流时,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许是他坚持的一种态度。从另一方面看,崔健也很单纯,只要他按照自己的逻辑把一些事情想明白,他就是正确的。
人到中年的崔健,他的摇滚精气神是否还跟当初一样?当他像个思想家一样面对音乐、媒体、生活时,他又是如何去叙述这一切的呢?

Q :二十多年前你刚开始玩摇滚的时候,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子?
A :要是跟现在比的话,某一个脉络上应该是一样的,想尝试自己创作上从无到有的可能性,一件事不做两遍。我刚开始弹琴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写到《一无所有》的时候已经是若干首以后了,所以尝试不同的可能是我创作的主脉,在这点上我没有变化,以后也不会有变化。你要说不一样,那就是风格上的不一样,年龄的不一样,承受的东西不一样,着重点不一样,平衡能力不一样。
Q :看你的演出,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你唱新歌的时候,台下的反应不是很热烈,直到你唱《一无所有》,大家的劲头才会上来,最让人激动的还是老歌,听众并没有跟着你的感觉走。
A :我只能这样说,第一是个遗憾;第二,现场音乐文化实际上和前几年一样,有些方面发展飞快,有些方面处在暂停状态,甚至倒退。中国摇滚乐现场状态几乎没有发展,我们都演二十年了,到过很多地方,大部分听众还都是第一次听摇滚乐。我发现最好玩的演出是在北京的小地方演出,因为观众不愿意听老歌。我们演出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唯一一次,顶多有两三次,也是间隔五六年,到场的观众大部分还是新观众。我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人第一次听我的音乐?哗—手举起一片,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摇滚乐。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摇滚现象产生在媒体,是文字爱好者对摇滚关注的结果,让我们当时一刹那就走红了。真正的摇滚乐应该像西方那样从小型演出滚起来的,是积累出的一种文化。我问过很多人,每年在摇滚方面的消费有多少钱,百分之八十的人一分钱都没有,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摇滚乐。摇滚乐目前只是一种现象,根本不是一种文化。包括中国的一些乐评人,他们只是一种打口文化的产物,他们首先听了大量的打口音乐,打口音乐的特点就是它是外来的、廉价的,它的文化基础也是打口的,甚至它跟本地区的人格建设、文化嫁接几乎是零。
所以,这造成了中国摇滚乐是横空出世,不是从本土的基础一点点滚起来的。虽然我是以本土的摇滚形象出现在中国摇滚歌坛的,但我的出现形式是横空出世,并不是一个积累过程。当我写了《红旗下的蛋》以后,我就厌恶了这种横空出世的位置,我试图把两脚落在地上,这个感觉就像将军开始当兵了,要解决具体问题了。可是很多人并不愿意关注士兵,他们还是愿意服从于一种权威和势力。
我发现, 80 年代后期我们自由创作的状态正好符合当时商业文化,就那几年是个平衡点,从大众政治文化过渡到大众商业文化,那几年正是我们出山的几年,我们受到的关注是自然的,不是炒作出来的,不是由一个政治群体或商业群体操作出来的。打口文化就是左手扶着西方的东西,所谓知识分子所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的先锋艺术;右手拿着中国的古董。如果两手一撒开,他们都是人格缺陷,支撑点没有了。我称这种艺术家为打口艺术家,他们从无到有的过程是空白的。在西方不是,西方经过了几百年,从他们的艺术品里,你能感觉到他们个人的支撑点,它们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它是个人的。如果你单纯地说它是西方的东西,很容易让中国人讨厌,因为这属于列强文化。在东方人眼里为什么没有成为列强文化?是因为它是个人的,能发现它们从无到有的发展脉络。

Q :那你想怎么去当好一个士兵呢?
A :也许是自我否定的过程决定了我一时去选择这个,更重要的是我的创作心态是以起伏交错的曲线发展,这段时间与那段时间不一样,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当我掌握作曲方法的时候,我喜欢 Hip-Hop ,喜欢独立完成一些工作,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我的创作方式。首先我对拿刺刀的工作比较感兴趣,我对每一个细节感兴趣。我记得姜文说过的一句话,很启发我:“才华人人都有,但就拼最后的百分之五。”我很幸运我生长在这个国度里,我很高兴中国有抵制外来文化产品的机制,当然这种机制对它自身创作也有限制。如果打口文化成为洪水了,成为主流文化,我们的艺术家会像香港一样,丧失自己的支撑点。我觉得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音乐基本上是这样,他们没有那种文化从无到有的过程,他们都是拿来主义;韩国、日本也是这样。再好的制作,再好的听觉快感也满足不了你内心人格的快感,所以这就是我选择做士兵的过程。
Q :现在人没有支撑点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可能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你想去改变它是不可能的。
A :你说的是结果,对我来说,我改变一个人我就高兴。我干吗要去做名利双收的事情?我从来没想过,所以这是我选择当士兵的原因。今天有个记者问我,你做音乐不是为了大众吗?我说不是,我就为我自己啊。
Q :你在一次演出的时候说:“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猛兽,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我要把这把刀子献给你们。”你在创作上也在参照西方的东西,而且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没有你的出现,大家对摇滚乐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今天你又说西方的东西让我们丧失了支撑点。
A :这最起码是我阐述我的观点第二位以后的,不是第一位的。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从形式上讲,西方摇滚乐像洪水一样,但是首先感动我的还是个人的东西,我第二位才想到是西方文化。如果中国摇滚乐永远失去个人支撑点的话,它永远只是单纯的一把刀子,在这一点我不愿进入一种诡辩的层次,偏要从逻辑上去吻合这两种说法,我觉得这就属于咬文嚼字了。

Q :可能有人玩摇滚、听摇滚没有你说的支撑点,他听了之后很兴奋,可能就去唱摇滚了。你现在想明白了,所以你才觉得在演出时遇到那样的尴尬。
A :你在解释一种现象,单独听摇滚和单独唱摇滚之间的区别,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这完全是不矛盾的,只不过是一个层次问题,只有去创作的时候才会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虽然说过“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猛兽,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但我还没有失去我的观点,我要强调刀子的意义,我要牢牢地插在这个土地上。
Q :你刚才说中国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是从一个政治文化向商业文化转变的过程,那时候商业文化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商业上的成功其实并不带有更多的欺骗性,那时候任何文化成为一种现象都是很单纯的。
A :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的传播媒体本身就有欺骗性,很多媒体都是以欺骗为目的的,不少媒体都存在一种红包制度,红包制度就是鼓励非个性,有红包制度就是在鼓励共性。在这个年代个性不美,你想从无到有创立个性,就是丑恶的。根本就没有理想,谁去挖井谁是傻冒,谁去卖水才是真正的时尚。
Q :这就是你在这张专辑中对文字工作者进行批判的原因?
A :我刚才差不多都说了,他们视社会问题不见,专拣软柿子去捏,所以红包制必须批判,实际上它就是反对个性。
(本文为《只有大众,没有文化》部分书摘)

书籍信息
书名: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作者:王小峰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日期:2015.8
本文由luowang于2021-04-17发表在落网音乐落网记忆落网电台,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本文链接:https://lw.oooc.cn/post/1626.html